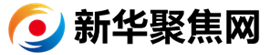刘浩歌:从农民到作家,永远扛起乡土文学创作大旗
在乡土文学创作的道路上,有这样一个执著痴迷的追求者,他把对故土的眷恋、对乡亲们的厚爱凝于笔端,无怨无悔地讴歌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。他,就是扛鼎乡土文学创作大旗的山东作家刘浩歌。

微山湖畔“荷花”开
关于刘浩歌的乡土文学作品,人们有着较多的阅读愉悦和艺术感受,然而更值得人们称赞的是,他在面对生活窘况时,不但能坚持文学创作,而且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放到发现、培养农村文学新人和推动乡土文学的事业上。
1986年10月,刘浩歌倡导成立了荷花文艺社,并担任社长,集合起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共同探索、耕耘。滕州市和微山湖周边几个县市的文学青年纷纷带着习作赶来求教。在许多日夜里,刘浩歌和他们交朋友,谈文学,帮助他们修改作品,还多次到家乡的中小学作报告,鼓励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中学生勇闯文学殿堂,把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收入他主编的《新星》丛书和作家文库丛书。
为了编辑修改会员们的作品,刘浩歌曾多日熬夜,竟致累的病倒住院。亲友们心疼地劝他:“你这么累这么苦为了什么?”刘浩歌笑了笑:“为了让咱土生土长的乡土文学走向全国!”

2001年刘浩歌为弘扬乡土文学,扶植和培养文学新人,面向微山湖的父老乡亲、面向人民大众,自己出资并自己编辑、设计、校对,创办了《荷花》杂志,担任社长兼总编辑。从此,他冒严寒,顶酷暑,不顾一切为杂志奔波着,忙碌着,一期又一期的出版着,使一大批有才华的农村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。
在荷花斋,刘浩歌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,每天都挤出时间来接待登门造访者,还要阅读来稿来信。一名在西北轻工学院读大三的滕州籍学生孙缓缓在来信中说:“作为你的一位小老乡的确被你顽强的奋斗精神所感动,也深深敬佩你热爱家乡的一片赤子之情…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,很想得到你的指点。”刘浩歌在复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和成长经历后,真诚鼓励她:“你酷爱文学并坚持业余创作,那就大胆地去追求吧!莎士比亚说过,上帝把亚当贬落到人间后,所制定的戒律第一条就是要用自己的血汗换取面包。成功和辉煌来自于艰辛和磨难……活就要活出一种气概,一种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志士之气。”刘浩歌用他的人生经历,更是用一种精神,时时在激励后来者。
作为一个从农民成长起来的乡土文学作家,刘浩歌生活并不富裕,仅靠以文养文的笔耕收益难以维持杂志的开支,他却个人出资几十万元,成功地举办了“浩歌杯”全国乡土文学大奖赛,他有一个酷爱乡土文学的赤子之心,他是一个强者,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贴近人民的作家。

情系乡土 妙趣横生
对于故乡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赞颂,刘浩歌从来是不惜笔墨的。在这些普普通通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身上,刘浩歌寄予着一片爱恋之情。刘浩歌的小说,就像一首田园诗,轻轻地勾起曾经的过往与记忆,悄悄地诉说着逝去的似水流年。它温馨又温暖,质朴又真挚,事无巨细,娓娓道来,无论家长里短,还是街谈巷议、乡间传闻,都一一落入笔端,诉说着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乡土故事。
正是因为有这种接地气、贴着人心的写作,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写荷花飘香的家乡、写微山湖畔的乡亲们,因此刘浩歌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,是一种清新的、纯朴的气息,氤氲着微山湖畔的泥土芳香。
作为一位农民子弟,刘浩歌对父辈身上的落后意识也进行了善意的讽刺和批评。《“弯弯绕”的黄粱梦》构思奇巧,诙谐生动,入木三分,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,称得上是一篇新的“醒世恒言”。我们从“精灵鬼”张老贵、“呱呱鸟”李满财的身上看到了存在于某些农民身上的自私、贪小便宜等旧习,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们可憎,只觉得可笑又可爱。
刘浩歌乡土文学兼有题材的传奇性和人物的平凡性,使他的作品在吸引人的同时,也不会使读者有离奇怪异之感。有的从篇名上就可看出故事的传奇习惯,如《神秘的金宝盒》《“铁拐李”遇仙记》《“弯弯绕”的黄粱梦》《张老三奇遇》《死人喊冤》《傻子和他的俊媳妇》等,这反而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传奇性是我国大众文学的重要支柱,但要使这种传奇性经得起推敲,为读者接受,不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,就要在塑造人和事上下功夫。刘浩歌在继承宋人话本和“三言二拍”优秀传统的同时,剔除其中的荒诞倾向,努力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的道路上探索,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、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典型人物,使作品的传奇性扎根于肥沃的泥土之中,有了可靠依托。
刘浩歌的作品在从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中汲取营养、推陈出新方面是十分明显的,《“铁拐李”遇仙记》受到民间故事“田螺仙子”的启发,《“精灵鬼”卖油》中的张老贵“负荆请罪”源于《将相和》和《水浒传》,《借媳妇》脱胎于传统戏曲……老梗新谈,让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和现实意义。

刘浩歌作品的特色还在于兼有故事结构的悬念性和叙述的平易性。悬念是牵动读者思绪的重要手段,而叙述的平易性恰恰延伸了这种悬念性,这正如层层剥笋,不紧不慢,娓娓道来,直到真相大白。刘浩歌往往在故事的开头就提起悬念,很快就抓住你的心,使你不得不读下去,看个够。如《寡妇门前》的开头:“微山湖畔有个荷花湾,湾里出了不少新鲜事儿。就拿刚死了丈夫的苦瓜嫂说吧,不知为啥,突然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。近几天,赖福和蔡旺两个光棍两种表现:赖福半夜三更老在苦瓜嫂院墙外头转悠,而蔡旺却笑眯眯地在苦瓜嫂家出出进进,仿佛是这家的主人。有人摇头说:‘等着瞧吧,寡妇门前的热闹戏要鸣锣开场了!’”又如《“精灵鬼”卖油》的开头:“在微山湖畔的一溜十八村,哪位不认识卖香油的‘精灵鬼’张老贵,不知为啥,近几天大伙再也听不到那又尖又油的卖香油的声音了。张家祖传的小磨香油突然停了业,使得一些好奇的人不断打听小道消息。然而,张老贵的嘴巴却像贴上了封条,一字不吐,半缕不露。”
语言的乡土味和口语化也是刘浩歌作品的一大特色。是否注重语言的地方色彩,能否熟练地使用方言俚语,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小说家能否写好乡土小说的关键。只有真正源于民间,源于生活,深入地掌握这些最有生命力的语言,小说才能真正达到妙趣横生、奇趣天成。
刘浩歌的较长篇幅的人物对话大都写得很精彩。这些家长里短的“闲言碎语”使人读之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。歇后语、夸张语、诙谐语的运用也很成功。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从古典小说、民间说唱艺术、大众语言中汲取养分。如在《婚骗》中:“那女人见自己惹下了大祸,早吓得一身冷汗,二目散光,三魂飞去,四肢战栗,五脏欲裂,六神无主,七情失控,八字倒运,九转愁肠。”“只见那女子乌黑的头发黑亮如漆,身材不胖不瘦,个子不高不低;瓜子脸,高鼻梁,弯弯的眉毛双眼皮,水灵灵一对杏子眼,雪白的牙齿好整齐。上身穿白底蓝花的确良褂,下身穿浅灰色裤子三合一。面容憔悴低头走,好似九月霜打的南山菊。”
作为新一代农民作家,刘浩歌的语言与前辈农民作家相比,更富有文采和抒情性。如:“两个相对无言,默默地互相望着对方的脸,只见窗外夜色的星月不知何时已经从天幕上清淡了,褪色了。夜如同淡紫色的花瓣,慢慢消融了一片白色的微光中,天蒙蒙亮了。隐约看见微山湖涌出一片灰白色的水光,在水尽头,出现了几片紫色的霞云,一轮圆圆的火球即将在湖面上升起来了。”(《傻子和他的俊媳妇》)“你瞧,刘家院子虽然不大,却成了名副其实的瓜蒌园:屋檐下,墙头上,一棚棚,一架架瓜蒌,枝肥叶茂,葱葱郁郁,绽放着一簇金黄色的花儿,摇着肥胖的绿叶,结满了圆滚滚的大瓜蒌。看一眼,喜煞人!”(《不是冤家不聚头》)
乡村生活的细腻传神在刘浩歌的笔下缓缓流淌,这些发生在当下的故事,是对我国农村鲜活的写照。正是这些琐碎得掉渣的讲述,呈现出了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。通过这些细腻而逼真的写实,农村的生活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,为我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愉悦的心情。

书写新时代的乡土文学
刘浩歌赠送我一本《刘浩歌乡土文学选》(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),收录了他历年创作的23篇文章,从篇幅看大都属短篇小说之列。他的作品从整体上焕发出的鞭挞假恶丑,颂扬真善美的伦理观念以及了解人、沟通人、尊重人、珍惜人、保护人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同他的经历是紧密相关的。正如刘浩歌在本书后记中所言:“我经历了那么多辛酸的事,听了那么多悲壮的歌,走了那么长坎坷的路,又面对着那么大一个浩浩荡荡的湖,又曾几度从生生死死的边缘上折回这清清朗朗的世界上来,该有多少情思,多少欢笑,要流泻于自己的笔端呢?”
广袤厚实的土地,不仅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和庄稼,而且生长世人最质朴的情感和最深邃的文学。于每个人而言,乡土和那里的父老乡亲是我们精神上的归依,但借助写作,则会更多地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温暖和满足。刘浩歌一直直面自己真实的家园,不虚妄,不矫饰。家园里的每一种事物,都散发着人性关照和人文气息。刘浩歌试图以一种略显拙朴的书写方式,以自己的文学和人生体验,去揭示乡土文学的深厚底蕴,展示神州大地民族淳朴、本真的状态,探问其背后的乡音、乡情源流与乡土成因。
刘浩歌说自己的创作一直都是立足于乡土大地。因为他对故乡的人民是怀着不可言说的无尽的挚爱,因此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的喜爱,这是一个相互互补、相互哺育的关系,微山湖畔的父老乡亲用自己的情感生活哺育了一个作家,这个作家又用他的作品反过来反哺他的故乡。